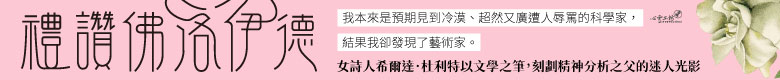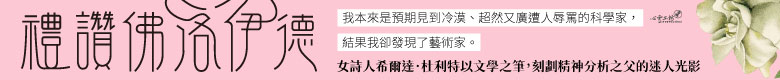|
禪心無所住 禪心是從渾然一體的主體感直接下手,用肉體的體驗直接搓揉。我們的立體感是一片模糊,猶如「北風吹窗紙,南雁雪蘆汀;山月苦如瘦,寒雲冷欲零」的直接體驗(《毒語注心經》)。日本白隱禪師這句偈,針對人的生活經驗,直接揭露了禪心的本質。
禪心的當下明白,不是對文字言詞的領略,而是對經驗本身冷暖自知的明白
禪心是當下的明白,但不是對主體的明白,而是對經驗自身渾然一體的明白。在《碧巖集》的第六則,須菩提與帝釋天的對話,正是說明這樣的明白。
須菩提岩中冥坐,入空三昧時,諸天雨花讚嘆。尊者:「雨花讚嘆,復是何人?」答曰:「我是帝釋天。」「汝何讚嘆?」「我重尊者,苦說般若波羅密多。」尊者曰:「我於般若,未嘗說出一字,汝云何讚嘆?」天曰:「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聞,是真般若。」
般若是覺醒的智慧,不是對文字言詞的領略。「無說無聞」是巨大的沈默與慧通。讓我們的肉體在寂靜之中,「入空三昧」是指進入深刻的無我。「無我」不是沒有「我」,而是冥坐時,自己與萬物渾然一體,不必區別我是誰,我與他人是本質地共存,撥開人我區隔的界限,我們直接與「北風」、「南雁」、「山月」、「寒雲」相交接,在交接中觸及實際,於其中求取活生生的經驗,概念的明晰則在其次。
經驗不是主體自身,而是主體洞燭的現象,默會靈識是經驗的根本覺察,文字是其道說。默會是主體的了然,主體早就在默會之中,才是禪心。
「禪」原本是不知不識,但是,人類從來沒有離開身體的知識,那是如皮肉相附的關係:知識做為語言的存在,早就是照顧身體實踐的支撐者,不僅僅是形諸文字,也在話語之中。由於離不開語言之思,「禪」於是有了心智,但是這心智緊緊地依靠在身體實踐之中;這與動物對世界的「本體知覺」不同:「當一條狗漫步在車行道之間,牠是以直覺閃避車輛;過了車道,牠把頭伸到樹叢底下的陰影,牠嗅一下,用爪子扒一下草皮,然後繼續走路……。」
在這「本體知覺」裡,我們看不到語言的意符(符號給出的意義),等於沒有人類所謂的心智或精神。但是,缺乏意符並不是人類的本性,隨便否決語言為心智給出的意義,並沒有為精神世界帶來何等了不起的建樹,相反地,人若僅僅沈淪在「本體知覺」,反而無所謂「禪心」。
禪師無法規避語言,他們必須運用比語言更能揭露世事無常的方法,那就是禪心──「無事」的心智
真正的關鍵並不在對語言的否定,而是對語言的徹底瞭解。語言本身既是為我們開顯了理解,也為我們遮蔽了悟。
把握了這個要旨,我們進一步說,即使語詞消失了,也無法取消人在大地的生活。語言的理解只是造就了「世間」──人活在世上的明白,而這世間的明白都由語言所託言的事情之中給出,所以,語言是「世間的」理解。
禪師面臨的問題並不是否認語言,而是否認「語言所給出的世間性」。做為「世間性」本身的語言有太多的邏輯與事物,直接從語言中汲取的事物,其實都不是禪師要的。
然而,禪師無論如何也無法規避語言,但他們必須有著比語言更能揭露「無事」狀態的東西。在這樣的處境之下,他們從語言自身表達的心智就是「禪心」──一種「無事」的心智。
讓我們從六祖惠能的例子來看看禪心。惠能禪師是從「應無所住」來啟迪禪的心智。「應無所住」的心智並不是從字句的說明,而是來自禪師生活的本質。禪師要「住」在哪裡?禪師說:「無所住」。禪師的「住」不是肉體的住居,也不是在話語中居住,而是「不住」──在無常之中漂泊於大地。
禪師的大地是禪師離開世間的「家」之後的「家」。世間的家,對禪師來說是遮蔽的地方。最大的遮蔽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在「關係之中」,我們歡笑與悲苦,我們忙著沖和在關係裡頭。在關係裡,雖然親情摯厚,有著世間的至情,它依舊遮蔽了大地。什麼是禪師的「大地」?在大地裡頭,聽什麼是什麼,做什麼是什麼,總是那樣直接當下的明白,而不是束縛在世間的情事當中。
於是,大地就是禪師「應無所住」的地方,在那兒,一切無事。大地不是某種心情或境界,而是越過世間的一種「所在」。在這個「所在」之處,禪師既不涉入事物,也不離事物,一切隨緣,即是隨緣,當即放下;即是當即放下,一切漂泊。雖說人在漂泊漫遊,足下卻沒有起念動心。在這個「所在」之處,生死大事遂成大功課。
活在「以死亡為立足點」的生活中,就是徹底的把「生命無常」當作心之所住,安之若素
為何說「生死大事是大功課」?並不是禪師要超越死亡,而是要以死為立足點的活。死亡是無法超越的,相反地,活在「以死亡為立足點」的生活,就是徹底的把生命無常當作「所住」。
禪師們用各種人間實相來說他們的禪心:「風來疏竹,風過而竹不留聲;雁渡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故君子事來而心始現,事去而心隨空。」
在「大地」的生活裡,眼前過去的事物是本質的出現,而不是一般世間的差別理念。在世間的生活裡,形體有俊醜,生活有富貴貧賤,成就有高低,事業有大小,才氣有高下,一切都以差別的理念來忖度一切;然而,「大地」的生活裡,人如裸體行走,片縷都是累贅,既不承擔,也不排斥。在大地裡,生命是不理會俊醜、貴賤的。在「生死大事」裡,眾生一切平等,做什麼事都沒有尊卑低下之分,就如同梁武帝對禪師達摩說:「我建了許多寺廟,復興了佛法,積了什麼功德?」達摩一句話頂回去:「並無功德」。
在「大地」的生活裡,禪心的經驗猶如「鮮活的初心」(beginning mind)。「初心」是一種乍然初見的喜悅,是把死亡納入懷裡之後,初次張開眼睛看到的世界:
當我第一次看到孩子睡著的眼睛,我看到睡眠撲翅飛息在孩子的眼睛──睡眠來自何方?有個傳聞說,睡眠居住在森林濃蔭的仙莊,在那兒,螢光蟲放著朦朧的微光;在那裡,懸垂著兩個迷人的羞澀花蕾。睡眠就從那兒飛來吻著孩子的眼睛。(泰戈爾《新月集》,糜文開譯,三民出版社)
我不引用禪師的話,卻引用泰戈爾的詩,主要是點明了一種「鮮活初心」的詩意。
「初心」裡的禪機正是大地的詩意。詩意從來不食人間煙火,它總是把自己與世間切斷,在大地的生命裡營生。例如,你知道孩子的微笑來自何處?詩人泰戈爾說:「一彎新月的初生之淡光碰觸著消散的秋雲之邊緣」,微笑就在那個碰觸中;你知道微笑最初是「生出於一個露洗清晨的夢中」嗎?
在人世間,生死是相隔、驚恐的;在大地的生活裡,生死是流轉如雲的;禪心不再陷溺於世事,而與自然相應
你知道在大地的生活裡,死亡是什麼嗎?我再度引泰戈爾在《新月集》的詩〈終結〉:
現在是我去的時候了,媽媽,我去了。
在寂寞的黎明之魚肚白的黑暗中,當你在床上伸出你的兩臂夾抱你的孩兒,我將說:「孩兒不在那裡」──媽媽,我去了。
我將變成清風來撫愛你;當你沐浴時我將成水中的微波,吻著你,又吻著你。
在狂風的夜裡,當雨點落在葉上起聲時,你在你床上將聽到我的低語,而我的笑聲將跟著閃電在哭著的窗中同進你房中。
如果你想念你的孩兒而且到夜深不寐,我將從星斗中對你唱:「睡吧,媽媽,睡吧。」
你睡著時,我將在流淌的月光中偷偷地來到你的床上。當你睡著了,躺在你懷抱裡。
我將變成一個夢,溜進你眼瞼微合的隙縫中,深入你睡眠之境;當你醒來驚恐地探視你周圍,我就飛出來像閃光的螢火掠入黑暗中。
當那盛大的「普佳」節到來,鄰人的孩子們都來屋子四周玩耍,我要溶化在笛的樂聲中,整天在你心中震盪著。
親愛的姨母將帶著「普佳」的禮物來問: 「姊姊,我們的孩兒呢?」媽媽,那麼你輕輕地對她說:「他在我的眼睛裡,他在我的身體裡,我的靈魂中。」
在大地的生活裡,生死是流轉的;在人世間,生死是相隔的。「生死」會流轉,因為禪師早就脫離人世間,已經不再活在事情裡頭,不必仰賴世事賦予他的生命意義,他早已看清楚人世本身就是障礙。
大地的生活與「自然」相應。相馬御風說:「雲朵靜靜地飄過天空,我也該靜靜地活下去。」這句話是禪師們最相應於世間的真言,靜靜的雲不給出事情,我端坐在世間,也該有坐在雲裡的感覺。與「自然」相應並不是拋棄文明而只做山野之人,而是重新把自己安置在自然裡頭──人不能規避一個事實:生存不是衝動,而是課題;生存不是自然,而是生命的歷史(命運)。大地的生活與自然相應,是重新把命運交到自然的生活裡,而不是僅僅回歸於自然。
人們活在事情的機巧裡,所以無法入詩
詩把人世的機巧完全斬除;禪師的話語是大地的驚蟄之聲
人的命運是做為人應該思考的課題,也就是對自身存在的探求。但是,人的生養過程總是在人間世,嬰兒必須是「在世撫育」,孩子必須是「在世學習」,人的知識必須是「在世之知」。所有這些人間世的文明是人成長的初次經驗,亦即,從嚴格的意義來說,人都是文明裡入世的人,必須活在人間情事當中。
大地生活裡的「自然」是出世間之後才看得見的處所,它常被誤解成童真的生活;恰好相反,大地的生活充滿的虔敬與感恩,都是來自對人的命運傷痕的悲憫。人必須體悟到自身命運的有限性。對死亡這個必然命運的徹底覺悟,而有「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的決斷。
在這樣的決斷裡,人發現大地。大地是天、地、神、人共同孕育的地方。人在天的星空之下,思及自己現實的一切;人在現實的生活不斷地褻瀆了大地,而有神的淨化;人在大地漫遊,與星空同住,成為大地的詩篇──禪心。
在五濁惡世裡,人們活在事情的機巧裡是無法入詩的。在近代的文明裡,詩意突然消失。詩是人類存在的另一種樣態,它把人世的機巧完全斬除,渴望著詩意的夢,徜徉在大地裡。禪師並不要作詩,而是他的話語如詩:堅定、純潔、淳厚與孤獨;所有的詩意來自人在事情破碎之處的聆聽,不再是人的風言風語,而是大地的驚蟄之聲。他聆聽到大地的存有,如歌的行板:
我原不知曉,在黎明之前我已受到你的撫觸。
通過我的睡眠,訊息慢慢傳到了我,這是淚的驚詫,我張開我的眼睛。
天空裡似乎為我充滿低語,歌聲沐浴了我的四肢。
我的心俯伏禮拜,有如一朵負露之花,我覺到我生命的洪流衝向那無窮。
(泰戈爾《橫渡集》,第卅八首)
對癡迷在世事裡的人,泰戈爾的詩有著難以理解的莫名其妙,但對禪師們來說,泰戈爾所說的一切「恰如實在」;這不是虛擬幻境,而是大地真實的言語。
活在事情之中的我們,虛耗著精神,沒有直接的生命感,
禪師卻全心全意活在大地漫遊中,當下即是,沈默坐忘
禪師赤足走在大地,越過田野,靜坐於山巒,他的行動早就是詩本身,即是田野之歌本身。把活著的生命越過世間,走向大地,並不是形式上的不食人間煙火,而是「心端坐如山,言談默如海」,整個活著的生命以大地存有的本質現出,放大光毫,宛如太陽。
禪師會歸返大地,是因為活在事情之中的存在是個假裝的生命,沒有直接的生命感;活在與他人關係的生命感固然美妙,依舊不能觸及自我的生命。就這點來說,禪師是很「獨」的,卻「獨」得非常實在,因為有種自我絕對的觀照緊密地成為禪師「存在之眼」,使禪師能夠體察真正的主體性。松原泰道說,禪師「在無人看到的地方,仍然能全心全意地盡最大的努力……不要醒目,不為人知,雖然是些微小事,只要是該做的,都規規矩矩地做好。」禪師走路,「每一步都會從腳跟上,吹起一陣涼風,這是因為對於自己『隨時隨地都是處在真理當中』的這個事實有了自覺,才會有這種感受。」(松原泰道〈步步是道場〉)
禪師行動裡的「獨」正是詩。詩的特性就是把事情的脈絡切斷,詩從來不說明白的事情,它總是在眼前的直觀放出一股力量,直透到生存的根柢。許多人無法讀詩是因為他們理解生命的方式都是由事情的脈絡下手,所以他們讀懂故事小說,而人的根柢卻在大地裡,那正是不住在「大地」的人永遠無法理解的──在「大地」裡,沒有精彩的故事可說,因為大地的活著不是對事情的描述,反而諸種詩意的譬喻較為切近!
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寒山詩〉)。
「竹影掃階塵不動」、「水流任急境常靜」、「月穿潭底水無痕」(說明「應無所住」)
三伏閉門一衲披,兼無松竹蔭房廊。安禪何必須山水,滅卻心頭火自涼(出自杜荀鶴〈題于夏日悟空上人院〉,松原泰道解說是:悟空上人房間的門關著,他身上披著一件破衣,而房子並無松竹的樹蔭可遮涼。坐禪不需要在安靜的山中或溪邊,只要把那攪亂身心的精神安歇,即使是炎夏也清涼。)
雖說禪師們喜歡用譬喻,但卻不可以拿譬喻來代表禪師的心,那只是禪師一時捕捉到的語言,雖然說是詩句,卻不是詩本身,真正的詩只有在禪師的行動裡頭。
禪師在大地行走,人聲、雨聲、風聲,陽光、月光、燈光;禪師的腳
穩穩地踏著大地,腳步聲在大地迴響;禪師聆聽一切,燭見一切,沈默坐忘。
當禪師沈默地坐下來,對我卻如驚雷巨響,我全身顫抖,不能自已,淚水也說不盡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