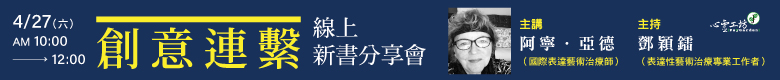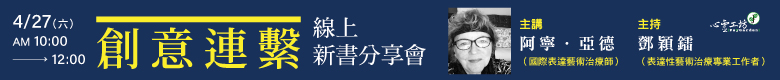|
第一章 同志伴侶的社會邊緣化 (1)一對同志伴侶經過了六個月的家族治療,在療程接近尾聲時,其中一位不經意的提到,下個星期就是他們的二十五週年紀念日。治療師很興奮地問他們要如何慶祝,兩人說他們沒有任何計畫。對於任何一對伴侶來說,在一起二十五週年都是了不起的成就,何況這對伴侶經過諮商之後,決定彼此再次做出愛的承諾。看起來,似乎應該舉行某種形式的慶祝。治療師知道,不論是以個人或是伴侶的身分,寇特和勞伯都尚未對家人、老闆或鄰居「出櫃」。但是,雙方的原生家庭似乎都知道寇特和勞伯不是普通朋友。過去幾年,雙方家庭都接納了兒子的「特殊朋友」。遇到家庭聚會和過節的場合都會邀請對方。當他們倆考慮分手的時候,勞伯的媽媽感覺到有什麼事情不對勁了,難過地說她這陣子不常看到寇特。他們在一起整整二十五年了,但雙方的原生家庭都從未公開地把他們視為「一對」。治療師還記得,療程一開始,第一次稱呼他們是「一對伴侶」的時候,兩人臉上驚訝的表情。
當治療師建議兩人舉辦二十五週年紀念日派對的時候,寇特和勞伯瞪著治療師,好像他是外星人。他們很快地就把這個建議丟在一旁,他們覺得吃個安靜的浪漫情人晚餐會是個好主意,於是開始討論要去哪一家餐館。(2)治療師聽著,心裡納悶為什麼這兩個人對於慶祝結婚紀念日的態度會這麼冷淡。他忽然想到,這兩人是在1971年認識的,那時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的石牆抗爭事件才剛剛過去兩年。當時寇特和勞伯正是住在那個地區。石牆酒吧的暴動被公認為是同志運動的濫觴。這是美國歷史上,首次有男同志結束了幾百年來的沉默,向主流社會爭取人權。雖然在1969年之前,同志伴侶必然已經存在,但是很少戀人會公開承認他們的關係。事實上,同志運動強調的是個人權益,例如同志的基本人權和性取向自由,而不是長期伴侶關係。接下來的十年,成千上萬的同志出櫃了,但是絕大多數的同志伴侶關係仍然不願曝光。治療師意識到寇特和勞伯親身經歷過那個時代,可能有他們獨特的角度,於是問起他們當時的情形。
男同志社群裡,少見關係長久的同志伴侶
寇特微笑地說起種種細節。他說,1969年夏天,當紐約警察進行臨檢時,他正在石牆酒吧裡。接下來的幾天,同志和支持者持續與警方對抗。寇特描述著自己當時的興奮和恐懼。那時警方常常臨檢同志祕密聚會場所,但是這一次的臨檢帶來的後果大不相同。
接下來的十年,最主要的社會運動就是性解放(sexual liberation)。隨著同志社群的公開化,男性之間的性行為越來越普遍。同志社群文化圍繞著性。當同志聚在一起的時候,不論是酒吧、私人俱樂部或是三溫暖,都不再有被捕的危險。在都會男同志社群裡,有許多不同的性伴侶成為常態。
1971年,寇特和勞伯在一個性愛酒吧裡相遇,一見鍾情。見面一年之後(勞伯提醒治療師,他們那時候不用「約會」這樣的字眼),他們同居了。一開始,他們就沒有要保持單一性伴侶。他們彼此公開自己在外面的性經驗,有時候還一起出去找伴。這樣的態度讓許多性對象及同志朋友大為不解。大家覺得,既然有了伴侶,卻仍然享有性自由,或是有了伴侶還追求性自由,是一件很「怪」的事情(3)。這些迷惑主要是因為文化認為正常的伴侶就是要有單一性關係。兩人被問煩了,索性在找伴的時候不再承認他們的關係,並且再也沒有以伴侶身分出現在任何社交場合。兩人在一起的前十五個年頭,他們甚至完全不認識其他的同性伴侶。寇特和勞伯不但對主流社會隱瞞了彼此的關係,對同志社群亦然。這件事治療師一直到療程將近結束的這個時刻才全然明瞭。
這兩個人之間(就像其他同志伴侶一樣)的主要問題就是無法建立一個可以讓別人明顯可見、他們自己也可以運用的伴侶界線(boundary),來界定他們兩人形成的社會單位。在男同志戀人之間,單一性伴侶往往不是主要的構成條件(Johnson and Keren, 1996)。如果單一性伴侶不能當作界線,那麼,什麼可以當成界線?什麼能界定他們的伴侶關係呢?
事實上,這對伴侶來接受治療的原因是勞伯愛上了外面的一個性對象。這個外遇的後果之一便是勞伯發現了他在長期關係中缺少的是什麼。當外遇發生時,這個經驗十分常見,也是伴侶分手的主要原因。對勞伯而言,他缺少的就是親密感(intimacy),不論是情緒上或是性關係上的親密感。當他們倆開始療程的時候,已經有五年沒有發生性關係了。他們都認為這是兩人之間最主要的問題。雖然外遇已經結束,但是兩人關係陷入危機,他們需要彼此釐清:伴侶關係到底代表什麼意義?
缺乏「社交氧氣」的伴侶關係
在一起二十五年,寇特和勞伯的關係完全沒有公開。在家族、異性戀社會、同性戀社會、認識的人之中,這都是一個祕密,缺乏認可。別的同志伴侶可以組成一個「自己選擇的家庭」("Family of Choice", Westin, 1991),由支持他們的異性戀者、同性戀者、單身的、已婚的朋友組成。當原生家庭不給予支持的時候,這個延伸家庭就益發顯得重要了。寇特和勞伯卻不是這樣。即使他們互許終身已經二十五年了,他們的關係卻一直瞞著別人。事實上,他們是隱形的一對。如此缺乏外在的社會支持──艾波爾.馬丁(April Martin)稱為社交氧氣("social oxygen",Martin and Tunnell, 1993)──真不知道這兩個人是怎麼熬過來的。
過去六個月,寇特和勞伯在治療師協助(4)之下思考他們的關係,以便決定是否還要在一起。治療師發現,絕大多數的時間裡,兩人都在思考他們到底算不算是一對?未來要不要繼續在一起?同志伴侶關係到底意味著什麼?【註釋一】跟著治療師,他們回想各種細節,發現彼此深深結合、在面對危機的時候他們多麼依賴彼此、他們分享一個共同的家、一起投資房地產、喜歡和對方相處、是彼此最要好的朋友。但是,他們算是伴侶嗎?
雖然如此親近、相處如此融洽,他們之間卻缺乏熱烈的情感和性愛。他們是室友、知己、投資夥伴,但是這樣就夠格稱為「伴侶」了嗎?隨著療程進展,兩人承認他們很少分享每天的生活細節,他們也從未學會如何解決彼此之間的衝突。過去幾年,他們漸漸發展出平行的兩個生活。
治療師開始要求他們試著用不同的方式相處,表露更多的個人情感,而不是採取慣有的封閉退縮。他們在治療時有了更多的互動,回家以後也越來越能交談,他們的情感變得益發親密。結果,這個親密導致了性關係的增加。這個結果並不是治療師一開始就有的計畫,兩人也都很驚訝。他們害羞地告訴治療師,他們又開始有性關係了,但現在的性比較像「做愛」,而不單只有「性」。療程接近尾聲時,兩人雖然在情感上重新做出承諾,但是仍然決定保持對外開放的性接觸。
回頭想想,治療師和兩人會談的時候,看到了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並挑戰他們繼續去深化這個關係,尤其是在情感上更親近彼此。治療師不只是解決了一些具體的問題,也正式肯定了寇特和勞伯之間的伴侶關係。這種肯定(5)是他們從別處無法得到的。缺乏認可他們的社交圈子──異性戀者視之為理所當然的支持力量──嚴重地傷害了他們的關係。他們沒有辦法建構作為終身伴侶的界線,而這正是伴侶關係的要件之一(Nichols and Minuchin, 1999)。正如非洲古諺所說的,需要整個村子一同扶養一個孩子,同樣地,也需要整個社群來維持和滋養一對佳偶。
【註釋一】請參考Green and Mitchell(2002)文獻中,關於男同志伴侶關係中常見的「模稜兩可的關係」精彩的討論。
首先因同志身分被放逐,之後因同志伴侶的身分被放逐
我們在第二章會進一步談到,男同志成長的時候,往往缺乏一個肯定他們生命核心存在(core being)的家庭或社群。男同志在童年及青春期都覺得孤立、寂寞、懷抱祕密(Savin-Williams, 1998),家庭通常無法提供男同志少年一個藉以逃避外界偏見的避風港。除非在情感上和經濟上都比較有保障了,否則他們通常不會讓家裡知道自己的性傾向。其他受歧視的族群都不曾在生命早期及建構認同感的時候,就如此受到「社會偏見」的毒害。例如,非裔美國家庭和孩子一樣擁有他們被外界歧視的身分特質──膚色,因此許多非裔美國家長會教他們的孩子如何調適、如何面對歧視(Boyd-Franklin, 1993; Hardy, 1993)。絕大多數的非裔美國孩子至少都能擁有一個沒有種族歧視與偏見的家庭。
相對地,在恐懼同性戀的社會裡,未成年的男同志在建構自我認同時,無法從家庭得到任何協助。家長極可能正是第一個歧視他的人。如果他露出任何典型的同性戀特質,表現出不典型的性別認同行為,例如玩娃娃或穿女生的衣服(Bailey and Zucker, 1995),父母大概會很緊張的送他去看心理醫生,而醫生很可能斷定他是性別認同障礙,要他的父母給他穿上長褲、教他打棒球。不論是顯著的或是隱藏不顯的文化訊息,都將同性戀視為病態,只有異性戀才是理所當然的,這也就是所謂的「異性戀主義」(heterosexism)。因此,大多數的男同志會將自己發育中的性傾向保祕密(6),直到他們感覺到足夠安全時才告訴父母,而這時候他們多半已經成年了。
男同志少年成長的時候被家庭孤立,他的身分認同無法得到支持。同樣的,同志伴侶的關係也缺乏社會支持。即便近年來經過革命性的變化,社會更能接受同性戀,但同性關係仍很少得到相當於異性關係得到的認可。不但主流社會歧視他們,即使他們的關係公開,而且已經被接受,家庭也可能歧視他們。即使家庭接納了這對伴侶,也還是會維持異性戀社會的偏見,將這對同性伴侶的地位放在其他已婚孩子之下。異性戀兒子一旦和新娘步上紅毯,他的伴侶關係立刻就得到認同和尊重,而對同一個家庭而言,同性戀兒子和另一個男人的伴侶關係卻需要多年努力才會獲得認可。在寇特和勞伯的個案中,當他們面對恐懼同性戀(簡稱恐同)偏見的時候,不但無法得到原生家庭的保護,也得不到其他同志的支持。在他們結合的那個時代,男同志社群並不重視或支持一對一的伴侶關係,於是他們從來沒有機會建構一個「自己選擇的家庭」。
寇特和勞伯二十五年的關係幾乎完全隱形,這聽起來可能頗為極端,尤其是在二○○二年,主流社會更加接納同性戀的時代。但是如果兩個男同志在同志運動形成之前就已經結合,或是住在美國的鄉下或小鎮上,或是隸屬於某個比主流社會更歧視同性戀的族裔、宗教或種族的話,他們的關係就可能完全隱形。何況,在某些時刻,同志伴侶可能刻意保持低調,假裝是兩個異性戀男人,以避免被人排斥、譏笑、羞辱或暴力對待。正如許多男同志少年假裝是異性戀者,以便安然度過童年及青春期一樣,當伴侶關係可能導致外界給予身體或心理的傷害時,同志伴侶也會暫時選擇隱形來求取生存。(7)其他被歧視的少數族群無法隱藏他們的特質,但是男同志可以並經常選擇隱藏他們的性傾向及伴侶關係【註釋二】。
出櫃不是單一事件,是終身無法停止的過程
這樣的隱形在心理上是有殺傷力的,因為它是羞恥感的溫床。同性戀傾向和同性關係的隱形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讓我們看到社會價值不但影響個人行為,並且傷害個人自我認同。一般而言,主流文化都是恐同的,大家寧願不要看到任何同性戀存在的證據。直到出櫃,男同志的身分會一直保持隱形,小心地不引人注意。這樣的社會壓抑會逐漸侵蝕自我認知,同性戀者會逐漸內化社會強行給予的較弱勢及邊緣化的身分(Hancock, 2000)。為了保持形象,將自己的同志身分隱藏起來的昂貴心理代價就是羞恥感。「出櫃」,拒絕隱形,是降低羞恥感的第一步。雖然表面上看起來,出櫃像是單一事件,其實它是一個終身不停的過程。隨著年齡日增,同性戀者不但要一直告訴身邊的每一個人,還可能需要「提醒」已經告訴過了的人!例如,對家人出櫃之後,男同志需要和家族達成各種協議,在這個議題上大家要公開到什麼地步。即使對家人出櫃了,有的家庭會要求兒子不要再提起這件事。因為持續的同性戀恐懼,同志談到自己的同志特質時通常會感到不自在,即便是出櫃之後,也會很識相的接受大家「不問、不說」的政策。
有些男同志會等到自己有了固定伴侶之後,才對家人出櫃,藉著已有伴侶的事實來建立身分認同。這個策略在某些家庭中會奏效(8)。例如,猶太裔青年亨利趁著回家探親,告訴母親自己不但是同性戀者,並且已經有了伴侶。他的母親聽到他不再單身非常高興,毫無困難地接受了他的性傾向和他的伴侶。她後來告訴兒子,他一直單身的這件事比他是同性戀者更讓她傷心。她非常重視家庭生活,強烈試圖說服這對同性伴侶領養小孩。相反地,對其他家庭而言,接受單身的同性戀兒子可能比接受他和另一個男人的關係容易得多。帶個男人回家說是自己的伴侶,可能嚴重違反家中「不問、不說」的默契。這些家庭能接受兒子是同性戀者,但不願意見到任何像兒子的情人這樣的證據。
最後,即使原生家庭很支持,同性伴侶仍會經歷隱形及邊緣化的問題。這種邊緣化可能是突然發生的。例如,本書作者之一和其伴侶的關係已長達十年,妹妹卻忽然要求他不要帶伴侶參加家庭聚會。這對伴侶早已得到家族默許,一直都有參加家庭聚會,這次同性戀恐懼之所以會重新出現,是因為妹妹的青春期兒子要帶交往半年的女朋友一起參加這次的家族聚會。這個外甥很擔心,如果舅舅帶個男伴參加,女朋友會怎麼想。雖然我們可以理解這個外甥的不自在,但是他的母親要求自己的哥哥把伴侶丟在家裡不帶去家族聚會,等於是要求哥哥在這個週末將自己的伴侶關係地下化。(想像一下,如果要求兒子將妻子留在家裡會是什麼景象。這個事件使得家庭互動緊張了起來:作者和妹妹起了衝突,他和他的伴侶都沒有參加那次的家庭聚會。雖然後來妹妹道了歉,也得到原諒,但是很明顯地,事件未被遺忘!)過了幾年之後的一個耶誕節,作者與他的伴侶從作者的母親那裡得到一個快樂的驚喜。她很會做針線,幫家裡每個人都做了一床拼布被子(孩子、孩子的伴侶及孫子)。作者的伴侶也得到了一床。如果作者的伴侶是個女人的話,也就不足為奇。結果這個小小的事件變成一個溫馨的慶典。直到今天,這床拼布被子都是一個象徵,一個可以看到的里程碑,這位伴侶已是不折不扣的姻親了。
【註釋二】因為在技術上保持性傾向的祕密是可能的,美國軍方真的提議並執行對同性戀「不問、不說」的政策。大部分的美國大眾假設,如果一個軍人是男同志,他們一定是單身漢。但是,有些人是有伴侶的,只是沒有公開而已。在目前的軍方政策下,個人的同志性傾向必須保祕密,同性伴侶關係當然也必須保祕密。如果一個軍人揭露了自己的同志身分,他的「出櫃」就可以成為被勒令除役的理由。
革命開始:同志伴侶可見度增加
(9)雖然在統計數字上,跟異性戀比起來,同志伴侶的數量較為稀少,但是同志伴侶在社會上已不再像以前那麼完全隱形了。確實,在過去三十年裡,同志伴侶可以公然同居,不啻為歷史上的革命性現象。然而,「同志伴侶」不但在主流社會是革命性觀念,連在同志社群裡都仍算是很前衛的。同志伴侶缺乏文化裡現成的模範、缺乏傳統上的伴侶界線、缺乏法律和經濟上的保障、缺乏社會全然的認可,必須一路掙扎地摸索建立並維持他們之間的關係。
在二十世紀後半期,兩個重要的社會事件發生了,促使美國的同志伴侶開始公開地生活在一起。首先當然是同志人權運動。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同志次文化已經開始在地下祕密凝聚了。孤立的男同志找到了彼此,開始形成一個「某種偏離常模(deviant)的性取向族群的心理認同」(Bem, 1993)。雖然主流文化和男同志都認為同性戀是一件羞恥的事,但這些「性罪犯」(sexual outlaws)(Rechy, 1977)仍然聚集在一起,形成一個暫時的、異議分子的身分認同,藉以減低社會的孤立感。但在1969年的石牆抗爭事件之後,男同志次文化開始轉型,從祕密集會變身為公開的少數族群,如果無法得到主流社會的接納,至少要爭取到認可。許多女同志及男同志運動分子呼籲拋棄主流引導的正常模式。在同志運動中,同性戀者不分男女,發展出一種態度:「如果要建構有效的認同,就必須擁有與主流社會對立的認知。」(Bem, 1993, p.172)
同志人權運動是讓男同志形成較為健康的心理認同,並在主流社會中能公開生活的最大功臣。如果沒有這個政治運動,我們懷疑精神醫學界和心理學界會不會分別在1973年和1975年正式將同性戀去病理化:從精神病症中除名(Bayer, 1987)。其後,在公眾論述中,較具肯定意義的「同志」(gay)一詞逐漸取代臨床上使用的「同性戀者」(homosexual)一詞。這一點以八○年代中期的「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尤為顯著「所有的新聞都必(10)須適合出版」,【譯註】他們終於允許「同志」一詞出現在他們引以為榮的新聞裡。這個語言上的轉變也讓同志對自己感覺好些,可以驕傲地認同自己的同志身分,而不是設法隱藏所謂病態的、羞恥的身分。但是,正如我們已經提過的,在一開始的時候,同志人權運動完全沒有認同或肯定同志伴侶的關係。
【譯註】這是「紐約時報」的座右銘。
愛滋病讓同志伴侶受到公眾注意
第二個促使某些同志伴侶公開化的主要社會文化事件是愛滋病(AIDS)的流行。在愛滋病流行之前,同志運動已經讓同志們覺得有權像異性戀者一樣享有各種權益,包括追求長期的伴侶關係。正如大衛.麥克懷爾特(David McWhirter)和安德魯.馬帝遜(Andrew Mattison)在1984年,正當愛滋病開始流行之初,出版的書《男性伴侶:關係如何發展》(The Male Couple)中所記錄的,同志伴侶的數量在七○及八○年代即開始安靜地增加,但是這些關係多半是祕密的。愛滋病讓這些同志伴侶受到公眾的注意。
正如石牆抗爭事件促使同志出櫃讓公眾注意到一樣,愛滋病讓同志伴侶也攤在陽光下。大眾媒體登載文章描述愛滋病如何影響同志伴侶間關係,這些故事也讓其他同志伴侶看到了這些同志伴侶。幾乎在隔夜間,同志伴侶有了少數幾個榜樣,也首次從大眾那裡得到同理心的對待。正如安德魯.蘇利文(Andrew Sullivan, 1996)寫的:「男同志成為疾病的犧牲品,同時卻矛盾地減低了文化上的犧牲。既然同志已經這麼倒楣了,就沒有必要再欺負他們。」(p56)雖然愛滋病危機使得有些單身、未受感染的同志從同志身分中退縮了,或是縮回櫃子裡或是保持無性的生活(Isay, 1989),但對於已經有了伴侶的同志而言,不論他們有沒有直接受到愛滋病的影響,愛滋病都讓他們的關係變得不那麼隱形了。
愛滋病剛開始流行的時候,主流社會並不認可同志伴侶,醫院工作人員不允許愛滋病患的伴侶照顧他或是參與有關的醫療過程。但是當流行擴大的時候,醫院開始肯定這種關係,讓伴侶併入被照護的計畫裡。例如,聖文生醫院(St. Vincent's Hospital)是紐約第一所注意到愛滋病患去世後,他的伴侶有獨特的心理需要的醫學中心。(11)醫院組成特別的哀傷團體,首次將失去伴侶的同志當成失偶的人(Greenan, 1987)。史諾夫(Shernoff, 1997)也記錄了同志喪偶的經驗。
還有,愛滋病一開始流行的時候,同志社群本身對於同志伴侶身分並沒有給予足夠的肯定。紐約的男同志保健中心(Gay Men's Health Crisis, GMHC)是一個前衛的社會服務機構,由紐約積極的男同志運動分子組成,主要工作是對抗愛滋病。直到1986年,在它廣泛的心理健康服務項目中,同志伴侶關係還未被包含在內。男同志保健中心將同志伴侶拆散在不同的治療團體中,進一步地讓同志伴侶關係變得隱形了。有愛滋病的人(Persons with AIDS, PWAs)都被分在支持性的治療團體中,他們的伴侶則被分在另一個照護者團體中。很多年後,他們才開始讓許多對伴侶一起組成治療團體,幫助同志伴侶以家庭為單位面對愛滋病,而不是以兩個人的身分分開面對。
同志婚姻及領養小孩的合法化
就像男同志保健中心一樣,同志次文化本身──過度強調個人自由和自主性、青春、外貌,以及個人性衝動的滿足──都不鼓勵一對一的關係。最近,有些同志伴侶流行舉辦互許終身的儀式,有人推動同志婚姻及領養小孩的合法化,已經引起部分同志社群的批評,認為這是在模仿異性戀結構及價值(Warner, 1999)。正如海若.庫登(Harold Kooden, 2000)寫的,男同志似乎常常在跟其他人說:「我們有不同的生活規則,你們的規則不適用在我們身上。」(pp.130-131)。直到今日,年輕的同志聽說有同志已經同居四年了,還會感到相當驚訝,若是聽到長達十五年以上的關係則會完全無法置信。
即便目前社會對同志伴侶關係仍然感到不自在,合法的歧視也仍然存在(1999年美國的維護婚姻法﹝Defense of Marriage Act﹞規定合法婚姻必須是兩個異性之間的婚姻),即便同志伴侶必須忍受從社會排斥到暴力毆打的種種邊緣化經驗,同志伴侶的數量仍然不減反增。有人曾說,自古至今,雖然社會強烈禁止並嚴重處罰同性戀,同性戀卻一直存在於各個文化中,這表示同性戀必然是一(12)種生理上自然存在的性傾向(Davison, 1991)。同樣地,我們也很驚訝地看到男同志無視於社會強力管制禁止,還是堅持要建立並維持長期的同性關係。不論性傾向如何,就像每個人都有強烈的生理衝動想要在性方面表現自己,每個人也都會強烈地需要依附別人,形成親密關係。正如約翰.鮑比(John Bowlby, 1979)寫的,依附現象是自然的,是「從搖籃到墳墓」都會存在的現象。並且我們會看到,依附現象在同性之間就如同長期異性關係之間一樣的運作(Mohr, 1999)。
關於人格發展的理論中,艾瑞克.艾瑞克森(Erik Erikson, 1950)寫到,一旦一個人在青春期和青年早期達到穩定的個人身分認同之後,下一個階段的發展就是形成親近的伴侶關係。艾瑞克森在寫他的理論時,心裡想的是異性戀者,但這些基本階段也適用於同性戀者。格林(Green)、貝廷吉(Bettinger)和柴克斯(Zacks)(1996)閱讀了許多關於男同志希望有固定伴侶的調查研究報告之後,做出結論:「認為大多數男同志寧可單身只是一個迷思。」(p. 214)更進一步來說,艾瑞克森的理論中,有了固定伴侶的下一步就是綿延子孫的慾望,這在異性戀關係中自然就是生小孩了。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同志伴侶試圖收養小孩或安排代理孕母。這個社會現象在幾年前還是聞所未聞呢。
同志關係、同志家庭和傳統的伴侶關係、家庭關係有相同之處,也有相互牴觸之處。我們需要覺察到異性戀和同志伴侶之間的相似與相異之處,治療師需要接納這些相異之處。這本書就是給家族治療師使用的新手指南。
同志伴侶與眾不同的問題
寇特和勞伯的例子讓我們看到,對同志伴侶而言,除了常見的隱形和缺乏社會支持的問題之外,家族治療師還可能碰到另外兩個問題。其中一個問題是許多同志伴侶選擇多重性伴侶(Blumstein and Schwartz, 1983)。這個選擇和傳統的(13)伴侶關係相衝突,可能讓接受傳統訓練的家族治療師不知所措。對於選擇多重性伴侶的同志而言,互許終身意味著情感上的支持、依附、可靠,而不是性的忠誠。事實上,同志伴侶的這三個議題──隱形、缺乏社會支持、常見的多重性伴侶──使他們和異性戀婚姻不同,因此,同志伴侶想要建構界線的難度更高。伴侶及家庭都需要界線,他們自己和別人才知道如何將他們視為一個社會結構單位,有他們自己的規則和組織(Minuchin, 1974)。
正如寇特和勞伯的例子顯示,與異性戀者相較,男同志伴侶的第四個獨特問題是情感表達和保持關係都特別困難。在寇特和勞伯的例子裡,他們不善於表達自己的感覺、不會表示親密和愛意、依賴強勢操作的方式解決衝突和處理兩人的差異。不論性傾向如何,主流文化都會不斷強化男人的強勢雄性(alpha male)行為。在涵化過程裡,大部分的男人都希望自己是強壯的而不是虛弱的、獨立的而不是依賴的、主動的而不是被動的、不妥協的而不是容忍的、理性解決問題的而不是情緒性的。商場及官方用語充滿戰爭式的詞彙,顯示背後支持強勢雄性行為的心態,例如惡意購併(hostile takeovers)、牛市(bull market)、熊市(bear market)等等詞彙。美國文化不獎勵男性之間互相忍讓的行為,在追求利益的時候,資本主義鼓勵人們對別人具有攻擊性的行為。如果男人在社會中顯示出「女性化」的行為──例如容忍、妥協、同理心,尤其是對其他男人的時候──就不符合社會賦予男性的角色。
正如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很多丈夫想跟妻子親近相處的時候會無法忘掉自己的男性角色一樣,許多男同志也有這個問題,只是更為嚴重,因為他們是想和另一個男人建立親密關係。也就是說,男同志無法豁免地會被強大的男性性別涵化(male gender acculturation)力量影響。確實,正是因為男同志成長的時候,對於需要別人、女性化、「娘娘腔」(sissy)這些議題變得過於敏感,他們可能發現自己很難在成年男性的伴侶面前顯露出脆弱的一面。因為他們在早期的家庭關係(14)和朋友關係中經歷過脆弱,於是長年發展出情感上的自給自足,擔心可能再度遭受到羞辱,因此,和另一個男人的親密關係就變得充滿挑戰。
我們的臨床經驗顯示,已婚的男性想要在妻子面前顯露出自己敏感(甚至脆弱)的一面時,會經驗到相當程度的困難;但是要一個男人對另一個男人顯露自己情感上的脆弱,則會是加倍的困難。社會允許男人顯露脆弱情感的少數場合之一,就是和女人的親密關係。也就是說,社會認為在與異性的親密關係中,男人可以顯露出自己脆弱的一面並表達自己的感情,這是可以接受的,雖然並不被鼓勵。有些男人即使在面對女人的時候都無法顯露出脆弱的一面,因此我們相信,一般男人要對另一個男人顯露出脆弱的一面則更為困難,不但因為社會對同性之間的關係具有同性戀恐懼,也因為男同志會抗拒將自己的情感託付給另一個男人。
有些人(Green et al., 1996)認為,男同志和異性戀男人是「不同的性別」,因此暗示男同志在情感和維持關係上可能困難較少。研究顯示,一般的男同志和異性戀男人比起來,較具有雙性特質(androgynous)(Kurdek, 1987)。雙性特質的人具有男性的自信和女性的連結性。事實上,具有雙性特質的男同志會比較容易維持情感上的連結。格林等人(Green et al., 1996)針對沒有接受治療的人口做出調查,比較了女同志、男同志和異性戀伴侶,結果男同志伴侶比異性戀伴侶擁有更強的凝聚力和彈性(女同志伴侶則表現更佳)。和性別角色的理論相反,男同志伴侶並非最不親密的族群,異性戀伴侶才是。是什麼原因讓他們的關係較佳呢?是因為他們比較具有雙性特質嗎?或是因為他們較不依賴僵化的性別角色?這一點還需要將來繼續深入研究。
然而,我們在治療室裡見到的男性,不論是異性戀或同性戀伴侶,他們的關係往往面臨極大的困境,這可能是因為他們的性別訓練特別強。對於兩個男人而言,形成親密關係的困難則更為複雜。簡單的講,最常見的男同志伴侶之間的問題就是如何照顧到(15)彼此的需要(而不傷害任何人的面子)、如何維持一個親密熱情的長期關係。當然,這些掙扎在異性戀伴侶之間也常常看到。然而,解決這些掙扎的方式卻有所不同。對於異性戀者,社會的約束會讓他們努力待在一起解決問題,但是男同志伴侶一碰到問題就會考慮分手。還有,在同志圈裡比較能接受在主要的伴侶之外,還能在外面尋找其他的性對象。
我們的模式:為同志伴侶調整結構派家族治療
經由寇特和勞伯的例子可以看到,我們基本上是採用薩爾瓦多.米紐慶醫師(1974; Minuchin and Fishman, 1981)的結構派家族治療三階段(加入、實際演出、打破平衡),但是和同志伴侶工作的時候,會加以改變。首先,治療師在治療一開始的時候──從第一次會面就開始──就必須特別強調加入的階段,將同志伴侶關係視為如同異性伴侶關係一樣是合法的社會單位。許多同志伴侶已經將自己的邊緣性地位內化了,可能預期治療師會批判他們、將他們視為病態且不把他們的關係當一回事,治療師必須在治療初期特別強烈地表達接納的態度。這個強烈的加入過程本身就會開始在同志伴侶身邊形成一個界線,將他們視為正式的社會結構。
舉例來說,強烈加入男同志伴侶的作法包括:(1)從一開始就視個案為「一對伴侶」,如同對待異性戀伴侶一樣;(2)認知到同性和異性伴侶的不同,很自然地問他們是否選擇單一性伴侶、為什麼會做這樣的選擇、兩人目前的遊戲規則是什麼;(3)問他們在親友眼中,他們的關係是什麼樣的關係;(4)特別要問他們的紀念日是什麼時候、為什麼選這一天,雖然同志伴侶很少會去紀念兩人正式交往的日子,但是幾乎所有的同志伴侶(15)都會有某種紀念日;(5)當他們描述他們的關係被別人忽視的事件時,要直接表達同理心;(6)討論多重性伴侶的議題時,不要把它當作病態,在一般的異性戀婚姻諮商中,多重性伴侶幾乎都被視為嚴重的問題(Lusterman, 1995; Pittman, 1987);(7)問他們是否曾經有過互許終身的儀式,若是沒有,將來是否考慮舉辦;(8)如果他們還沒有孩子,問他們是否打算養育孩子。提出這些問題可以讓個案知道,治療師拿他們的關係當一回事。
還有,和同志伴侶工作的時候,如果他們缺乏很強烈的親密連結,也不會表達情感的話,在治療的中期及晚期(實際演出、打破平衡)治療師就必須積極協助每個人變得更脆弱、更開放、更能對伴侶的脆弱做出回應。大部分的男同志對自己的核心自我、脆弱、需要同性的支持、情感和愛都感到羞恥。伴侶治療可以改變這一切的情感經驗,兩個人直接向彼此表達自己的需要,期待彼此都會專注地聆聽並做出回應。
在這一點上,我們的治療方式挑戰了性別的刻板印象,打破我們認為應該如何對待彼此的固有模式。相親相愛的伴侶關係可以讓個案不再需要將核心自我隱藏起來。在成長階段,男同志往往覺得在世界上只能靠自己。這個信念在童年及青春期求取生存時很有用,但是在發展健康的伴侶關係時卻有害。在同志伴侶治療的過程中,這個信念需要被積極地質疑和挑戰。
總而言之,強烈的加入同志伴侶時,我們會表露出對許多男同志伴侶必須承受的邊緣化及污名化經驗的尊重和同理心。但是在治療後期,我們需要挑戰他們,使他們的關係更完滿、更親近。男同志伴侶治療的一個功能就是協助他們接受彼此高層次的情感表達,而不使用刻板印象中的男性模式──強勢、威脅、羞辱、不理會。藉由挑戰男同志伴侶嘗試新的和與彼此更親近的人際互動方式,治療師創造了一個引進新意的治療過程。我們將男人對於依賴、親近、互相照顧的需要視為正常。以這個角度來看,治療也是一種政治宣言,挑戰社會認為正常的(如果不是唯一可以接受的)異性戀家庭結構。治療師製造機會讓男同志嘗試非傳統的、比較不依照美國文化中男性刻板印象的行為。【註釋三】
【註釋三】顯然地,我們的模式也可以應用在異性戀伴侶治療上,異性戀的男性也需要被逼著嘗試新的行為模式。
治療師的態度
身為和男同志伴侶工作的家族治療師,我們必須持續地檢視我們對同性戀的態度,尤其是同性戀恐懼及異性戀(主義)偏見,因為我們都成長在美國文化中,不可避免地會接收到這些訊息。即使本身就是同志的治療師,也自認為完全支持同志伴侶關係,但如果他們對於接觸並鼓勵同性之間的親密會感到不自在的話,就可能在不知不覺中投射出同性戀恐懼的偏見。沒有人──包括心理治療師──能夠在這個文化中成長,而完全沒有內化部分的同性戀恐懼、異性戀主義,以及對於「性別不正確」的行為(不符合性別角色的行為)感到不自在。我們碰到過號稱很會治療同志的心理治療師,卻一直詢問個案同性戀傾向的源頭,即使個案沒有興趣,還是一直探究他是如何變成同志的,這些問題暗示了同性戀傾向是病態的。雖然這些治療師在原則上是支持同志的,但他們的技巧卻隱然有點同性戀恐懼的味道。有幾次,我們在專業會議中提出報告時,遇到明顯的歧視與偏見。有一次,我們放了一段影片,是第七章中提到的一對同志伴侶之間一段很感人的對話,其中一位正受愛滋病所苦,將不久於人世,觀眾席裡的一位精神科醫師很認真地問:「你跟這兩個人工作時,如何處理他們的同性戀傾向?」
我要說的是,支持同志的心理治療師不管在治療個人的時候,立意多麼良好、多麼有效(18),在治療同志伴侶的時候,都會被迫面對自己的偏見,這在個人治療裡是看不見的。我們已經討論過,只要沒有認真交往的伴侶,有些家庭可以很順理成章地忽視孩子的同性戀傾向。但是一旦兒子戀愛了,開始公開與另一個男人出雙入對,這個家庭隱藏的同性戀恐懼就會全盤浮出檯面。親眼看到兒子跟另一個男人這麼親熱、看到兩個男人睡同一張床、讓兒子的伴侶參加家庭聚會,都試探著他們接受的程度。即使治療師真的覺得自己沒有同性戀恐懼、認為自己沒有特別偏好異性戀價值、相信性別角色確實限制了所有的人,但當他看到──何況還要鼓勵──兩個男人在他的辦公室裡表現得非常溫柔、依賴、親熱的時候,還是可能覺得不自在。但我們深信,同志伴侶治療往往就是要這樣。
以我們的經驗,和男同志伴侶──尤其是非常受到傳統男性角色涵化影響的人──發展治療模式的時候,需要用鼓勵、允許、直接的挑戰來刺激個案,引導他們以更溫柔、更有感情的方式對待彼此。治療師的干預會打破伴侶之間的平衡狀態,引進新意。婚姻治療師在治療異性戀伴侶時會例行地鼓勵更親近的互動,但無疑地,即使是同一位治療師對於以同樣的方式介入兩個男人的關係時,還是會感到焦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