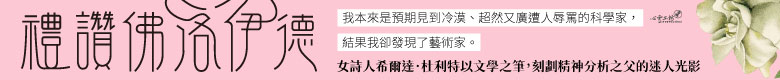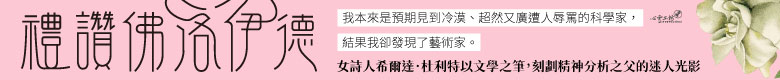|
第一章 六歲時的戰爭 我的人生歷經兩次誕生。
第一次出生,我不清楚。我的身軀於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來到人世,在波爾多。這是人家告訴我的,因為我自己沒有任何記憶,所以只好相信人家說的。
我的第二次誕生,我可是記得很清楚。一天夜裡,我躺在床上被一群武裝人士包圍逮捕,他們是來抓我處死的。我的故事就從這一夜開始。
逮捕
六歲還不懂什麼叫「死」,還需要一、兩年才會有時間觀念,知道什麼是終止,一去不復返。
當法吉太太說:「如果你們放他一條生路,人們就不會認為他是猶太人了。」這話讓我很感興趣,原來這些人不要讓我活下去。這句話讓我明白為何他們叫醒我時都拿槍指著我,一手拿手電筒,另一手持手槍,頭戴氈帽,臉戴墨鏡,束起衣領,十分嚇人!原來要殺小孩時要這樣打扮啊。
我對法吉太太的舉止感到不解:她穿著睡衣,把我的衣服塞進一只小行李箱。然後她說:「如果你們讓他活命,人們就不會說他是猶太人。」我不知道什麼叫做猶太人,不過我聽到的是只要不說出來就可以活。簡單!
一個看似隊長的人回答:「必須消滅這些孩子,不然他們會變成希特勒的敵人。」原來我是為了一項我將來會犯的罪名而被處死。
這一晚誕生在我身上的人,因為這樣的場景而出現在我的靈魂裡:要拿來殺我的手槍、夜裡戴的墨鏡、在走廊上肩扛步槍的德國士兵、以及特別是這一句奇怪的話,說我未來是個罪犯。
我當下的結論是那些大人不是認真的,生命是引人入勝的。
若我告訴你,在這難以想像的一夜過後,我花了很久的時間才發現我當時只有六歲半,你一定不相信我。我需要社會的力量來提醒我該次事件發生在一九四四年一月十日,波爾多猶太人被大逮捕的日子。關於我的第二次誕生,我需要來自外在的頭緒來幫助我記憶,好理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去年,我接受一家基督教電台RCF之邀來到波爾多,上一個文學節目。女記者陪我走出去時說:「走右手邊的第一條路,走到底你會看到電車車站,可以坐到市中心的梅花廣場。」
那天天氣好,錄節目的過程很開心,我感覺很輕鬆。突然間,我驚訝地發現有些影像忽然出現在我腦海中:那個夜晚,在街上,武裝德國士兵的路障,以帆布覆蓋的幾輛卡車停在路邊,還有我被推進去的那輛黑色汽車。
那天天氣好,莫拉書店還有人在等我赴約。為何我會突然想起這麼一個遙遠的過去?
來到車站,我看見一棟大型建物的白色石頭上刻著「病童醫院」。突然間我想起法吉太太的女兒瑪歌下的禁令:「不要去病童醫院那條街,那邊人很多,可能有人會舉發你。」
我的心一驚,半路折返,發現自己剛剛經過亞利安—拜瑟隆斯街。我剛剛不知不覺地經過法吉太太的家。自一九四四年後我再也沒見過她,可是當我看到一個徵象,零散鋪路石間冒出的草,或是台階的樣式,讓我又想起我被捕當時的情景。
即使一切都好,卻可能突然間因目睹某物而喚起過往的記憶。日常生活、與人會面、各項計畫會把那場悲劇埋藏在記憶裡,但是只要一被喚起――鋪石路間的一株草,砌得不好的台階――就會讓你想起一段過去。就這樣,你以為已經忘掉的,原來一點都沒有消逝。
在一九四四年一月,我不知道這件事會改變我的人生。是的,我不是唯一一個有死到臨頭經驗的人――「我死裡逃生,死亡成為我的一項人生經驗……。」――可是對六歲的我來說,一切都會留下痕跡。死亡印記刻在記憶裡,變成人生發展的新主導者。
有意義的回憶
父母過世對我而言並非重大事件。他們本來在,然後就不見了。我不記得他們是怎麼死的,可是我收到了他們消逝的印記。一下子沒了父母該怎麼活?這不是受苦;人在荒漠沒有受苦可言,就只有死路一條。
我對二戰前的家庭生活記得很清楚,兩歲的我剛開始嘗試說話,可是我仍保有影像的記憶:我記得父親坐在廚房桌邊看報紙。我記得屋內中央有一大堆黑炭。我記得我很羨慕同樓鄰居在烤肉。我記得我那位十四歲的叔叔賈克用橡膠箭射我的額頭;我記得我哭得好大聲,好害他被處罰。我記得母親一直殷殷期待我會自己穿鞋。我記得波爾多碼頭停泊的大船。我記得看到有人背上扛著好大串的香蕉。我記得還有其他上千幕沒有對白的獨幕劇,形成了我至今對戰前所保有的印象。
有一天我爸爸穿著軍隊制服回來,我感到好驕傲。從檔案資料我得知他加入了「外籍義勇軍」,那是由外籍猶太人與西班牙共和黨組成的軍隊。他們在蘇瓦松(Soissons)作戰,大吃敗仗。當時的我不知道狀況。今天,我會說我以有一位軍人父親為榮,可是當時我不喜歡他的軍用橄欖帽,我覺得那突出的兩個角很可笑。我那時兩歲,我是真的有這樣的感覺?還是我是在戰後才看到他的照片?
接連的事件讓你看到來龍去脈。
第一幕獨幕劇:德軍在胡塞爾街附近的大馬路上行進。我覺得好壯觀,士兵一起踏步的節奏展現一種強大的感覺,讓我很高興。音樂揭開行軍的序幕,每匹馬的身體兩側掛著大鼓打著節奏,令人生畏。有一匹馬滑了一跤,士兵們把馬扶起來,恢復行進秩序。這是很棒的悲劇,我很驚訝地發現我周圍的幾個大人都在哭。
第二幕獨幕劇:我跟媽媽去郵局。德軍以小隊的方式在街上走,沒有武裝,沒戴軍帽,甚至沒繫軍用腰帶,我覺得他們這樣沒有士兵的樣子。其中一人伸手到自己的口袋裡,抓出一把糖果給我,我母親搶過來把糖還給士兵,一邊還罵人。我佩服我母親,又可惜吃不到糖。她對我說︰「絕對不可以跟德國人講話。」
第三幕獨幕劇:我父親自軍隊放假。我們在加倫河邊散步,我的父母坐在一張長椅上,我在玩球,球滾到另一張有兩個士兵坐著的長椅邊;其中一人撿起球還我,我起先拒絕拿,可是他面帶微笑,我就接受了。
不久,我父親重返軍隊,母親再也沒見過他,我的記憶開始遲鈍。
稍後,當瑪歌來救濟單位領我的時候,我的記憶才恢復。我的父母不見了。我回想起自己曾無視母親的禁令,還是開口跟士兵說話,而這一連串的記憶不禁讓我這麼想:假若我的父母死了,那應該是因為我無意中透露了我們家的地址。
一個孩子怎麼解釋自己的父母失蹤,當他根本不知道有反猶太法令的存在,而唯一可能的理由是他違反禁令:「絕對不可以跟德國人講話。」就是這一連串的片段回憶讓你重組過去。重組分散的記憶後,我的結論是我的父母是被我害死的。
在幻想中,一切看似真實:公牛的肚子、老鷹的翅膀與獅子的頭,可是這樣的動物並不存在,或者說,那只在藝術當中出現。所有記憶中的影像都是真實的,記憶經過重組整理後會變成一個故事,每一個刻在記憶裡的事件會形成個人奇想的一個元素。
只有當我周圍有生命時,我才會保存記憶。我的記憶隨母親過世而消逝。而在聖喬治街上的幼稚園,我們的日子過得很精彩;瑪歌•法吉老師用她三歲的小演員們來演《烏鴉與狐狸》的寓言故事,我還記得下列的詩句讓我深感困惑:「烏鴉先生,在一棵棲息的樹上……。」我不懂樹怎麼棲息,還擺上一隻烏鴉,可是我還是全然投入我的狐狸先生角色。
有一件事情讓我特別生氣,因為有兩個叫弗蘭索瓦絲的小女生。我覺得每一個小孩都應該有自己獨特的名字來命名,我認為給好幾個小女孩叫一樣的名字,她們就沒有個性了。沒想到我這麼小就開始做心理分析!
自稱尚•博德(或拉博德?)
在家裡,不像樣的人生讓我們的靈魂麻木。在這個時代,當男人從軍去,女人就只能靠家庭了。一九四ま年代沒有社會福利。然而我母親在巴黎的家人不見了,她的一個妹妹,十五歲的珍娜,也失蹤了。沒有被捕的跡象,沒有遭到大逮捕,啥也沒有,她就這麼突然不在了,可以說是「消失」。
你也不可能工作,那是被禁止的。我模糊記得母親在街上,坐在一張長凳上,賣著家裡的物品。
我的記憶黑洞介於一九四ま年到一九四二年。我不清楚日期,而且時間的順序一直非常混亂;「我兩歲時被捕……不,不可能,我應該八歲了……不,戰爭已經結束了。」幾個極為清晰明確的影像在我的記憶裡揮之不去,我卻無法確定時間。
最近,有人告訴我母親在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八日她被捕當天的前一晚,將我安置在公共救濟所。我不想查證此事。我從來不認為她拋棄我,應該是有人事先通報她,她把我安置在那裡是為了救我。然後她獨自回家,在空蕩蕩的房子裡,沒了丈夫,沒了孩子,直到清晨被捕。我不願回想此事。
我在救濟所應該待了一年,我不知道,一點記憶也沒有。我只記得瑪歌來找我的那一天。為了讓我聽話,她帶了一盒糖,一直不停給我吃,直到她說:「沒了。」不再給我。我想當時我們是在一輛不知打哪來的貨車上,要去波爾多。
來到瑪歌家中,我的記憶就變得一清二楚。身為督學的法吉先生,氣得「面紅耳赤」。我裝出讓人印象深刻的樣子。法吉太太責備她的女兒:「妳去救濟所找這個孩子之前應該先跟我們商量才對啊。」
瑪歌在巴約納(Bayonne)教書的姊姊蘇珊,教我看客廳裡鐘擺大鐘的時間,還有像貓一樣優雅地進食,她說貓用舌頭小口小口地吃,不像狗一下子全吞下去。我記得我跟她說我不同意。
法吉一家人會很奇怪地圍著一台大接收機收聽:「葡萄太綠了……我重複……葡萄太綠了……」或是「小熊送了一個禮物給蝴蝶……我重複……。」刺耳的噪音使得這些話有時很難聽得清楚。我當時不知道那是倫敦電台,可是我覺得一群人圍在一台收音機旁認真地聽一些好笑的句子,不是太正經。
這家人給了我一些任務:維護花園的一小部分、幫忙打掃雞舍、去病童醫院附近車輛出入大門口的分發牛奶處領取牛奶。我每天都在忙這些事,直到有一天,法吉太太說:「從今天起你叫尚•博德。你唸一次!」
我應該是跟著唸了一次,可是我不明白為何我要改名。一位有時過來幫法吉太太做家務事的太太親切地跟我解釋︰「你要是講出你的名字,你就會死。其他愛你的人也會因你而死。」
每週日,瑪歌的弟弟卡米爾會過來同家人一起吃飯,他一出現大家就笑開懷。有一天,他穿童軍服,帶了一位年輕友伴回來,這個朋友客氣穩重,一頭捲髮好像綿羊,當卡米爾喚我做「『我要攀談』小朋友」(le petit j’aborde)而逗樂大家,這位朋友站在後面笑著問我︰「尚,你要跟誰攀談啊?」
我總是記不得我的假名︰博德?……拉博德?我總是搞不清楚。直到後來,當我在巴黎薩伯特慈善醫院神經外科實習時,有一個叫博德的年輕女醫生,我差點告訴她我在大戰期間就是用她的姓氏藏匿身分,可是我沒說出口,因為也可能是拉博德吧?而且,還要解釋一大堆呢!
光復二年後,當學校恢復我原本的姓氏,我才真正意識到戰爭結束了。
我的阿姨朵拉收留了我,整個法國都在歡慶,由美國人來定調。他們年輕瘦削,只要他們一出現,家家戶戶都充滿歡喜。他們的哈哈笑聲,他們有趣的口音,他們的旅行故事,他們的生活方式,都讓我感到著迷。這些人分送口香糖,組成爵士樂隊,女人們搶著要無縫線的尼龍絲襪與好彩香菸(Lucky Strike)。一個戴著小圓框眼鏡的年輕美國人覺得鮑赫斯(Boris)這個名字不好,俄國味太重了,他幫我取名鮑伯(Bob),這個名字帶來光明,它象徵「恢復自由」。大夥兒都鼓掌,可是我接受這個名字時沒有喜悅。
等我成為醫學院的學生,我又恢復鮑赫斯這個名字。此時,我覺得朵拉阿姨應該不會聽到人家叫我這個名字,沒有惹她傷心的危險。對她而言,那還是一個危險的名字,而鮑伯則代表重生,與我們的解放者美國人一起歡慶的意思。對我僅存的家人來說,我還是需要躲藏的,可是遠離他們之後,我可以變回我自己,用我的真名,恢復我的身分。
兩位童軍造訪之後,在瑪歌家的日子也告終。一天夜裡,我被叫聲與光線吵醒。法吉先生在睡夢中過世,法吉太太變得消沉,蘇珊回巴約納教書,瑪歌於週一早上也消失了,我想她是去拉內默藏(Lannemezan)當小學老師。房子變得安靜,沒有聲響,沒有好笑的廣播,沒有人來訪。就因為我叫博德(或拉博德?)所以我就不能去領牛奶,那變得很危險,我可能被人檢舉……。檢舉?
有一天,來了一個我不認識的女士。瑪歌說:「她會帶你去看你爸爸。」我爸爸?我以為他失蹤了。我整個麻木了,既無喜悅,也無悲傷。這個世界真沒邏輯。那位女士的左胸上有一個用黃色布料縫的星星,亮亮的,鑲有黑邊,我覺得很漂亮。瑪歌指著星星問:「您戴著這個好嗎?」那位女士回答:「我自有辦法。」
我們一路上沉默不語,悶了很長一段路來到梅里尼亞克(Mérignac)營區。那位女士走向守在營區入口的士兵,一邊解開她的圍巾,用安全別針將之別在上衣上以遮蓋那顆星星。她向士兵出示文件,然後我們走向一個木棚。一個人在那裡等我,他坐在一張木床上。我幾乎認不得我的父親。當然,他說了一些話,然後我們再度啟程。
戰後過了很長一段時間,我收到他的十字勳章,還附上亨西格(Huntziger)將軍簽的一張證書:「勇敢的士兵……在蘇瓦松前線受傷。」這就是我父親為何坐著的緣故。他在病床上被捕,是地方首長下的令,他被帶到梅里尼亞克營區,然後再送到德朗西(Drancy),再到奧斯威辛(Auschwitz)集中營。
第二天,我聽到瑪歌小聲地說,那位女藥劑師(原來這是那位女士的職業)一回家就看到蓋世太保在等她,結果她跳窗。
說話是危險的,可能會害你沒命。可是閉嘴也讓人不安,因為讓人覺得沉重的威脅感不知打哪兒來。誰會檢舉我?該怎麼保護我?我以為法吉家的人過世都要怪我,因為他們對我很好。
家裡變得陰沉寂靜,幾個月來都沒什麼事情發生。我當時六歲,我不會讀書也不會寫字,沒有收音機,沒有音樂,沒有朋友,沒有文字。我躲在客廳裡繞著桌子打轉,頭昏眼花給我一種奇特的存在感,讓我平靜下來。等我轉久了,累了,我躺在沙發上,舔我自己的膝蓋。一九九三年,當我跟世界醫生組織去布加勒斯特(Bucarest)時,我發現被遺棄與感官上被孤立的孩子,也同樣會出現這種以自我為中心的舉動。
也許是因為這樣,讓我覺得被捕是件值得高興的事。人生回來了!我不怕軍人為了封鎖亞利安-拜瑟隆斯街所設下的路障以及成排的卡車。現在我覺得這景象很生動:為了逮捕一個孩子出動軍隊!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我被推進去的車子裡,有個男人在哭。他的喉結非常突出,動來動去,我看呆了。
在猶太教堂前,我們被排成一排排。我們一進門,就被帶往兩張桌子。一個穿皮靴的軍官兩腳分開,站在兩張桌子中間,就像一部爛片裡的情節。我記得他用一根棍子,指示我們該走向哪一張桌子,這個選擇代表什麼?我聽到有人說:
「要說自己病了,他會叫我們去登記入院的那張桌子。」
「萬萬不可,」其他人說:「要說我們很健康,才會被送去STO,去德國工作。」
一進門,我就看到左邊隊伍排的那張桌子後方是那位有著綿羊捲髮的童軍,卡米爾的朋友。我脫離隊伍朝他走過去,他一看到我,嚇了一跳,椅子倒地,他大步離去。
這時我才明白是他舉發我的。
(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