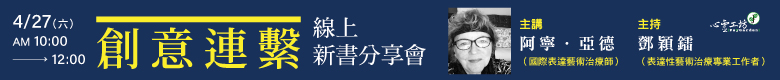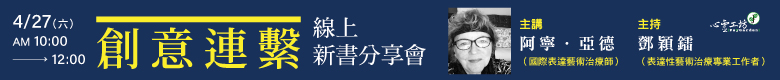|
| 書系 |
|
| | 成長學苑 |

-
心靈工坊成長學苑
忙碌城市中,一個美好的身心靈成長空間,以多元化的分享、活動與課程,跟大家一起追尋健康、探索生命、深化體驗,展開靈性視野,擁有快樂飽滿的心靈力!!
|
| |

|

|
|
| 活動訊息 |
歐文.亞隆,和趙旭東、李鳴、王浩威 一場跨半球的史詩級對話
|
|
2016-05-15 大學糖
直擊美國當代精神醫學大師歐文.亞隆與心理治療界史詩級對話!
5月13日,我們舉辦的直播《對話歐文•亞龍》引來了數十萬人次參與,一時間刷爆朋友圈。很多同學在聽課的同時,也進行了速記整理。但因為缺乏校對,所以內容不完整,準確率也比較低。
為了能讓大家複習能有一個更精准的版本,大學糖緊急整理了文字稿,邀請老師連夜審核校對後,正式發佈。以供大家學習。
文字稿版權歸大學糖所有,歡迎轉發到朋友圈,轉載請聯繫後臺哦。
▼
【趙旭東】中國的朋友們,晚上好!三藩市的朋友們,早上好!歡迎大家來到萬人講座!我們大學糖來組織的這個公益講座,現在開始。我們這個節目製作了很好的預告,所以我想開場的介紹我們可以省掉很多的時間,要把今天晚上的時間多留給亞龍先生,讓他多談一談,另外我們這邊的專家:王浩威醫生,李鳴醫生也有機會多多發言。
現在我就按照原來設定的程式。我想簡要介紹一下亞龍先生,他的介紹本來是已經在大家的材料裡了。今天我們有一個流程方面的安排,我先來提一兩個問題,請亞龍先生講一講,然後另外兩位專家和他進行交流對談。現在我想大致地談一談我最近瞭解亞龍先生的作品,有這麼幾個印象:總體來講就是他是一位精神科醫生出生的心理治療師,是一位非常具有人文情懷的助人者、療病者,他對哲學有非常深的造詣,還有他是一位受過科學訓練的高產作家,他的文筆非常好,知識非常淵博,他是一位跨了多個學界、多個門類的大學者。我看過他的一些視頻材料,介紹他的心理治療技術,非常溫暖,非常有藝術性。
對於今天晚上的這場講座,我非常期盼!按照我現在得到的數字,已經有四萬多人正在觀看我們的會談直播。我們今天的翻譯是我們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哲學倫理學的博士生閃小春女士,她做一部分同傳,做一部分交傳。
現在我就向亞龍先生提一個問題,請他自由發言:聽說您在寫你的自傳,現在如果回顧一下您的生涯,您最希望和我們中國的醫生、心理治療師、心理諮詢師說一些什麼?你最深的感受是什麼?我們曾經看過您在心理治療裡邊如何處理死亡焦慮,死亡恐懼症的話題,我們今天也想問問這方面的情況,有請亞龍醫生!
【歐文•亞龍】謝謝,我現在確實在寫一本很厚的書,關於我個人的傳記和職業生涯,你們知道我現在這個年紀非常適合寫這樣的書。我現在寫作也遇到一個麻煩,那就是,有點擔心如何結束這本書!因為我寫完這本書之後我的腦海裡面已經沒有其他的書了。因為在過去的30-40年裡面,我的腦海總會有不斷的素材出來出新書,但是這是我的最後一本書了,這有點非同尋常。
首先談一下我從事精神科的職業生涯,我在上大學的時候接受過所有的科學訓練,因為那個時候醫學特別熱門,那個時候我也是跟著熱潮進入大學學習精神科。但是我從小就有一顆文學的心和文學的夢,我在青少年時期就讀了很多書本,廣泛閱讀了世界各個國家的名著,那個時候還經常寫詩,或者其他東西,讓老師貼在黑板報上,這點可能和當時的很多同學是不同的。我上大學讀了醫學院,接受科學的訓練,我上了三年大學,之後又上了三年的醫學院。
我來講一個故事,這個故事我也寫在我的回憶錄裡面。我在讀醫學院時,每一個學生都會被指定一個病人,我們需要和這個病人工作12周(編者注:在《歐文亞龍的心靈地圖》中說的是8周)。然後每次學生都要呈報他們病人的案例報告,而呈報的物件就是系裡面很資深的精神分析師和精神科醫生們。精神科醫生對這些學生非常的尖刻和犀利,總是批評他們做得不好。所以輪到我來呈報案例的時候,我就很擔心,他們會批評我些什麼呢?於是我決定,我不按照標準的案例報告的程式來彙報,先寫症狀,之後是歷史等這些東西。取而代之的是,我決定來給他們講一個故事,因為我非常善於講故事,那個時候用講故事的方式來呈報案例是比較時尚的做法。
當時我23、24歲,遇到的是一位女病人,我報的是我們的初始訪談。她是一個非常擔心害怕又非常害羞的女性。我問她為什麼想來看精神科醫生,她的主要的問題是什麼?這故事是發生在1950年左右。她對我說:“我是一個女同性戀。” 然後我不知道什麼是女同性戀,於是就真誠的問她:我不知道什麼叫女同性戀,你可以給我介紹一下嗎? 要知道那個時候處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我也不是對這方面知道得特別多,於是我就允許她來教育我:到底什麼是女同性戀?她們會怎麼做?又會有怎樣的不同?就這樣,我們建立了一個很好的工作關係。我們的治療關係非常好,她非常遺憾我們只剩下幾次的會談時間。當我的故事講完之後,實際上我已經準備好,來歡迎和擁抱這些資深的精神分析師和精神科醫生給我的批評。然而奇怪的是,他們沒有一個個的批評我,而是出現了一片沉默,然後我們的系主任說你的故事太美,太好了,我覺得沒有什麼要增加的,其他的資深精神分析師和精神科醫生也表達了同樣的意思。他們從沒聽到過這樣的彙報,一個學生講了一個故事,連案例的基本情況和資訊都不講。
這就是我當時進入這個領域的情況,當我的案例報告結束以後,每個人都給了我非常積極的回饋,其實我做得非常簡單,就是講故事而已。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萌生了一個想法——也許我可以用講故事或寫小說的方式給這個領域做一些特殊貢獻。我是在位於巴爾的摩的約翰霍普斯金大學醫學中心接受的住院醫師培訓,它的位置靠近華盛頓,是一所歷史悠久的大學。
當我剛剛進入這個領域的時候,精神醫學的治療其實只有兩個框架或者說方法,一個是精神分析,另一個是藥物治療。這兩種方法我其實都不喜歡,在那個時候藥物治療能夠提供給我們的並不是很多,而精神分析我也不是很喜歡,很多的精神科醫生都必須要接受精神分析師的分析,我那個時候的精神分析師是非常正統的精神分析師。我的精神分析師是一位女性(編注:Olive Smith),她也有自己的分析師,她的分析師是美國當時非常著名的分析師萊特曼,而萊特曼自己是接受過佛洛德本人分析的。從這個層面來說,我也可以說是佛洛德的嫡傳弟子。我當時接受的精神分析是一週四次,持續三年,共700次分析。我的分析師是一個非常正統的分析師,在做分析時,我躺在躺椅上,看不到她,而她在我身後,一直只做一件事——就是只做解釋,非常經典的佛洛德模式。她不給展現有關她的任何東西,和我也沒有建立個人關係,因此我從自己的個人分析裡體驗最深的是,這種治療方式不是很好。
當我在上大學二年級的時候,當時出版了一本羅洛•梅的書,英文名字叫《Existence》,我不知道在中國大家知不知道。(【王浩威】國內有翻譯本。)當時我覺得這本書非常有意思,後來我個人也和羅洛•梅有一些關係,幾年後,他成了我的治療師。當羅洛•梅去世的時候,我有參與他死亡過程的工作。他的這本書給我們提供了除了精神分析和藥物學模式之外的心理治療的第三種方法,一種存在主義治療的方法,從很多的哲學裡面延伸出來的方法。如果我們回顧心理治療發展歷史,一般都說心理治療起源於19世紀,從佛洛德開始,大約在1890年左右。但是我並不是這麼認為的,因為我覺得心理治療開始得更早,在之前的2000多年的歷史裡面,在歐洲很多的哲學家,同時還包括來自中國的許多哲學家,都提到很多關於生和死的哲學內容。
從那時起。我開始接受哲學的教育和訓練,我在約翰霍普斯金大學上了很多哲學的課,開始去瞭解很多這方面的古老的智慧,西方哲學源頭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圖、蘇格拉底、伊壁鳩魯等這些偉大的哲學家。我開始發展了自己的兩種治療方法:一個方法是哲學的方法,另外一種是團體治療的方式。這兩種方法是非常不同的,不同之處在於哲學的方法我更多強調的是一些哲學家的思想,團體治療的方法更加注重人際之間的關係。在那個時候美國的精神分析界也開始發展出了新形式的精神分析,和經典的佛洛德模式也非常不同,不需要一味追溯童年和早年歷史。我不確定大洋彼岸是否熟悉這些人物:沙利文、霍妮和弗洛姆。(【王浩威】大部分的作品都有翻譯成中文。)
我非常喜歡霍妮,她對我非常重要,人際關係取向治療對我非常重要,因為這些人往往很難建立非常親密,非常強烈的關係,於是我就開始對團體治療越來越感興趣,我在約翰霍普斯金大學有一位老師叫弗蘭克(Jerome Frank),我從他身上學到了很多關於團體治療的方法。所以我是帶著人際關係的視角開始做團體治療的。我不希望團體的成員去關注自己過去的歷史,我希望他們更關注在團體當中和每個團體成員之間的關係,而且這種關係是如何和他們個人的症狀產生關係的。這樣做的原因是我把這個團體比喻成一個微小的社會小宇宙,核心的觀點就是他們的問題,他們在外面與其他人的關係的問題就會呈現在這個團隊裡面,他們不需要說什麼,就會自然呈現在這個團體裡面。所以我更關注的是團體中的此時此刻,更關注的是當下他們和團體其他成員的關係,包括個人和個人之間的關係。在我從事這個事業10-15年之後,我開始走向另外一個方面,我開始關注存在問題。我在講的時候有什麼疑問和問題可以隨時提出來。
【趙旭東】亞龍先生剛才說目前在寫的這本回憶錄是最後的一本書,記得您有一次演講時談到‘the last one(最新的)’和‘the final one(最後)’的差別,我想這本書應該是‘最新的’,而不是最後的一本書。我相信亞龍先生會有更多的作品出來。
【歐文•亞龍】(笑)其實我在說這句話的時候,我的朋友們也都會笑,在過去25年裡我不停講這句話,但是也許會有更多的故事出來,因為我還是在不斷地接診病人,在接診過程中會有新的故事浮現。
【李鳴】亞龍先生,我就著你的話題,因為你提到了存在主義,我很希望你能夠多談一點,作為一名存在主義治療師,你曾經說過:任何一位治療師,不管是什麼理論取向的心理治療師,都會從存在主義的主題中間獲得啟發和靈感,請你就這個問題給我們中國的治療師一些建議。
【歐文•亞龍】我寫了存在主義心理治療,而實際上我是寫給所有的心理治療師看的,因為我覺得所有的病人都會遇到這些問題,當然,並不是所有的病人來的時候都是來談這個問題的。有些是因為他們的人際困擾過來的,有很多人來是因為他們和先生的關係、和妻子的關係、和孩子的關係,或者是和上司的關係,這些都是在團體治療裡面經常會呈現的問題。但是還有一些病人只有我們從存在主義的根源考慮才可以更好理解和思考他們的問題。
我想到我這周早些時候見到的病人,是一個新的故事,我以前聽到過類似的故事。我的病人是一個男性,55歲的樣子。他是在另外一個國家,我和他通過SKYPE的方式連通。他非常成功,賺了很多錢。他是在一個非常有名的國際金融公司工作,但是他的主訴是非常抑鬱,他非常困惑,他不知道為什麼還要工作,因為他的錢一輩子都花不完。他開始討厭他的工作,因為這個公司唯一的意義或者目的就是賺錢,這是一個跨國的公司,是一個銀行。他越來越低落,他不想去上班,他和他太太的關係也開始惡化,所以我和他的工作的出發點就是對他來講生活已經沒有什麼意義了。
我問了他一個問題,我說:“你上一次覺得對你來做重要的,有意義的,很豐富的時候是什麼時候?”他告訴我,是青少年的時候,那時候他在寫詩和寫故事,雖然這些內容都沒有出版和發表,但是他覺得這是對他來講最有意義的事情。我從他的生活失去意義的時候,討論他內心有藝術家的夢和想法,他說他也開始思考,也許有一天從這家公司退休,60歲或者65歲,他也許會重新拾起青少年時期的藝術夢。我的工作的方向,就是讓他對自己有更多的覺察。我讓他在紙上畫一條生命週期的線,這條線一端是他的出生,另外一端是他的死亡,問他,你認為你現在在這個生命週期的哪個點。他就線上上一個點,說他的生命已經過去了四分之三了。我就問他,為何還要等十年才去做這樣的事情呢?為什麼不可以現在每個週末寫一點?或者每星期花半天時間寫一點?或者為什麼不參加一些寫作的課程?實際上我和他的工作就兩次,他原來有自己的治療師,找我只是諮詢,我更多是從一個自我轉化的角度和他工作的。
所以像我和這位病人的工作更多是關注在存在主義的核心主題:生命的意義。當然存在主義治療還有很多其他方面的主題,比如說死亡。我現在接待病人不是特別多,每天也就兩三位。有一些病人來找我是因為得了癌症,或者他們失去了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經歷過這些之後,他們開始思考自己的死亡問題。他們會做惡夢和其他很多症狀,當然並不是說每位病人來了就會談論死亡,因為存在主義還有很多其他的主題,這只是其中的兩個。
【王浩威】我能否問一個精神分析的問題?亞龍剛剛講的一個存在的問題,認為存在的問題其實比精神分析的歷史來得悠久。反過來講,有一些人就會認為說,是不是我們可以從存在的問題來討論所有的這些心理問題就可以了呢?也就是說,我們對哲學上存在的議題多點認識,再學一點會談技巧就可以了?也的確如此,在臺灣就“哲學諮商”這種流派,那這樣的話,反過來講,對亞龍來說,他學了那麼久的精神分析到底有沒有什麼用?它的意義又是什麼?
【歐文•亞龍】當然精神分析也有用,我剛才講的是一些特別的,一些特殊的病人,他們會特別從存在主義的方法獲益。還有很多的病人,他們的問題是早期童年的問題,更多是一些比較經典的精神分析的問題,我和這些病人工作的時候,我就會從這個角度去工作,使用的方法其實是根據病人而定的,看他們主訴和他們帶來的問題到底是什麼。
實際上我還是非常尊重佛洛德的,當我開始寫《當尼采哭泣》這本書的時候,我做了很多文獻的研究和調查。那個時候在尋找1882年在維也納有什麼樣的心理治療,但實際上是沒有的。(編注:所以這小說是以佛洛德將離開神經生理實驗室時所追隨的家庭醫師布洛依爾為尼采的心理醫生。)直到佛洛德出現,寫了他的一些東西,和他的思想,所以佛洛德是歷史上第一位精神分析師也是第一位心理治療師,是他把這些東西帶給我們的。
我現在的一個病人,他的主要問題就是他的腦海裡面不斷有一個東西,不是聽到一個聲音,而是腦海裡不斷地縈繞的想法:操你媽,操你的兄弟!(翻譯注:亞龍先生不確定在中文裡去說“操”這個詞是否合適,我覺得對我們的文化是非常合適的)所以我就和他講到童年早期和他爸爸的關係,我就會回到這個源頭,因為佛洛德認為所有強迫的想法的根源背後就是非常深的憤怒,尤其是指向父親的憤怒,所以我就沿著這條思路和病人一起工作,我就發現他對他的父親出奇的憤怒,因為他的父親一直在虐待他,甚至到現在。所以給病人工作的時候,其實我主要的關注就是回到他早期的生活,和他父母早期的關係,我更多的是去追隨病人的思路,而不是一定按照我的思路,讓他們追隨我。
這就是為什麼我總是認為心理治療師要接受所有主要流派的培訓,而不是只接受其中的一個。我覺得一個很有效的方法,當然這是我個人的方法,就是去接受治療,尤其是去接受不同流派的心理治療師的治療。我自己實際上接受過非常多的治療的,我剛才提到過,我剛剛開始是接受的經典的精神分析治療,當時分析了700次,持續了三年。第二次治療是我在英國的時候,那個時候英國政府對我不是很好,我非常焦慮,見了一個英國的治療師(編注:是當時在塔維斯托克的萊克勞夫Charles Rycroft),他是屬於英國精神分析的中間學派。第三次,後來我回到了美國,因為我和媽媽之間的問題,我又非常焦慮,那時候我就找了一位格式塔流派的治療師,他是皮爾斯的學生(編注:即邦嘉那特 Pat Baumgartner)。我就想看看格式塔流派的治療師怎麼做治療。第四次我當時和很多癌症病人工作十年之後,我自己非常焦慮,尤其是死亡,我就見了羅洛•梅,跟他工作了幾年。所以我會覺得自己從不同的治療流派中受益很多,學到很多。
【李鳴】亞龍醫生,你提到你聽說過很多心理治療學派的治療或者說是訓練,然後你還提出了注重病人的經歷和故事,也說了你自己在醫學院的經歷,而不是注重病人的症狀和表現,你能否在這一點更加詳細地給我們介紹一下?
【歐文•亞龍】關於這個症狀,其實我和佛洛德的觀點是很相似的,我覺得佛洛德也會認為症狀是有意義的,那麼症狀背後的意義是什麼?當然也許對於有些病人來講,僅僅關注他們的症狀也可以有收穫,但是往往這種收穫是非常短期的,他的問題還會在其他的方面冒出來。就是說也許和有些病人工作,他們覺得幫助他們做一些去症狀化的工作就會非常有效,他們會說:“喔,我已經知道症狀的意義了。”但是我會更加關注症狀背後的意義。在我的書《當尼采哭泣》裡面更多地闡述這方面的觀點,我們知道,書裡面的那位治療師,他一開始的時候就去做一個實驗,去嘗試一下:如果我只關注病人的症狀會怎麼樣,但是後面他就發現這樣是不會起作用的,所以後來他開始會去關注症狀的意義,症狀的背後到底有什麼。
當然也有一些治療的方法就是針對症狀而產生的,比如說認知行為治療(CBT),就是專門針對消除症狀而發展出來的,雖然也有很多文獻證明CBT對於幫助病人也是非常有效的,有很多相關的研究。但是這些並不是很長期的效果。現在CBT非常流行,尤其是醫療保險公司,他們非常喜歡這樣的方法,可以用很短程的方法去消除病人焦慮的問題,但是我個人選擇更加深入一點,也許你們覺得我比較老派。
【王浩威】我在想,也許講故事永遠都是很重要的。在心理治療的發展裡面,這些年來,有所謂的敘事治療,可以說是在心理治療中講故事的進一步發展。我想把這個問題再擴大一點,就是說,四五十年前,亞龍醫師他是這麼地勇敢,他敢突破當時精神分析一家獨大的狀態,放棄去拿精神分析師的資格,創出自己的這條路。他是怎麼看未來的心理治療?比如說像剛才談到的,他當年提出的存在主義心理治療,或是像現在有講故事的敘事治療,是不是我們每個時代都要找到自己的治療方式,來讓所有的我們正在面對的現在的問題也好,我們面對的現在的病人也好,才可以達到比較適合的照顧吧?
【歐文•亞龍】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是說有不同的流派針對不同的人群都會有不同的效果,確實是這樣。我現在有一位女性病人,她對於其他人完全沒有同理心,她說話一般不經大腦,從來不去想她這樣講別人怎麼樣想,別人會有怎麼樣感受,也就是說她從來不會告訴自己:我所說的這些話會對別人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我和她的個體治療中,就一起去探討這個問題,我見了她三四次的時候,有一次我問她,她的父親、母親以及他們之間的關係。她對我說:“你已經是第三遍問我這個問題了。” 她說的是對的!我記憶力沒有以前好了,但是她這樣說是很傷害我的感情的,所以我們就一起討論,是不是有其他的方法表達同樣的意思呢?因為實際上這就是給她帶來麻煩的真正問題,不管和她的朋友,家人還是上司。因為這個問題實際上是她最核心的問題,和我之間的人際關係的問題也是和其他人關係問題的體現。對於這樣的病人來講,我覺得最好的辦法就是團體治療,我想辦法讓她加入團體,但是實際上我讓她加入團體還是會繼續讓她做個體治療,因為這樣就可以消耗她的一些憤怒。
所以我會針對不同的病人選擇不同的治療流派,當然也有一些治療師,他們什麼流派都可以做得很好,比如說有的治療,有時夫妻有問題、孩子也有問題,他們都應該去做個別或團體治療,但是他們會採用一種聯合治療(conjoint couple therapy)的方式,也會非常有效,以前美國非常流行,現在不知道為什麼很少提到,可能消失了。
【王浩威】我解釋一下聯合治療。聯合治療是Virginia Satir佛吉尼亞•薩提亞提出來的,治療的方法就是比方說先生有一個個別治療師,太太也有一個個別治療師,兩個治療師又一起幫他們做夫妻治療,大概就是這樣。現在很少人這樣做。
【歐文•亞龍】就像我剛才提到的這位病人,我就會覺得她既要參加團體治療也要繼續接受個體治療。也許有的人覺得只參加團體治療就可以了,但是我覺得她可能需要有個體治療來去幫助她看到團體裡呈現的一些東西。
上星期我接診了一位病人,她是一位心理治療師。她非常害怕在公眾面前講話,就是我們講的舞臺恐懼。但是實際上每次演講都做得很好,她問:“我知道結果很好,但是為什麼會這麼害怕呢?”每次這樣的時候她都有一些驚恐的表現,雖然她是一個非常好的演說者。我並不想她再接受我比較多的心理治療,我可能會把她轉介給做催眠治療的同事,可能一次就可以解決她的問題;也許我會推薦她去接受精神科醫師的藥物治療,克服她上臺的恐懼。
【趙旭東】我接著浩威的問題,問一下,說到了每個時代可能會誕生一些和那個時代精神相關的療法,請問一下對系統思想、系統式的干預、系統式家庭治療怎麼看待的?在六七十年代,就在三藩市附近有個Mental Research Institute(MRI,精神研究所),現在還有影響嗎?(編注:趙教授這時拿出一本書,是瓦茲拉威克Paul Watzlawick傳記,封面就是他的照片。)
【歐文•亞龍】我可以談談這個叫MRI精神研究所的情況,實際上我剛才來斯坦福大學時,每週都要去那裡一天,那裡的人是非常非常有創意的,而且他們是非常與眾不同,可以同時有很多很多不同想法的人在一起,其中一個就是你剛才給我看的這個人:Paul Watzlawick保羅•瓦茲拉威克,實際上他是我的一個朋友。除了剛才提到的這個人,我在MRI還有另外認識的一個人就是Virginia Satir佛吉尼亞•薩提亞,她是家庭治療方法的一位創始人,我當時有家庭的個案是去見她的,整整一年的時間。Virginia Satir佛吉尼亞•薩梯爾有力量、非常有創意,就像軍用坦克(Army Tank)一樣,每次氣勢壓過來了;還有另外一個人就是Don Jackson唐•傑克遜,他也是一個非常有創意的人,他的特點就在於經常提出一些悖論的東西。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做治療的時候,有一個病人坐在治療室裡面很高的凳子上面,身上穿著長長的紅袍,就像皇帝一樣,一言不發。我們當時拿這個病人一點辦法也沒有,這個時候傑克遜走進來,他看了一下病人,就對病人深深地鞠躬,像臣子拜見陛下一樣拿出一把鑰匙給他,說:我的陛下,你自己有自己的鑰匙的。這個病人看了看他,說:我們兩個人肯定有一個瘋了。所以實際上我也去了MRI,我其實對他們非常熟悉,他們那個時候真的非常有創意,但是我現在對他們沒有太大的興趣了。
【趙旭東】李鳴,輪到你了,你接著提問嗎?
【李鳴】我非常希望能夠早日見到你的厚厚的自傳,因為我已經翻譯你的團體心理治療和住院病人的團體心理治療,我希望能夠繼續翻譯你的下一本書!
【歐文•亞龍】不要著急,其實快出來了,大概再有三四個月這本書就要出來。我每天都在寫,其實當我寫回憶錄的時候,我要重新讀我以前所有寫過的書,實際上有許多書是15-20年前寫的,所以有時候去重新讀自己寫過的東西是非常有意思的經歷。當我讀《當尼采哭泣》這本書的時候,我就會很驚訝,我真的不覺得現在的我還能寫出這樣的作品,這本書的作者真的是比現在的我還更好的作家。比如說這本書裡面我讓尼采按他的口氣來講話,但實際上我現在已經做不到這一點,也許我當時是讀了許多尼采的作品。
還有一本書是我最愛的一本,書名叫做《媽媽以及生命的意義》,有很多的評論者並不喜歡這本書,因為他們覺得我在裡面提到可以一隻講話的貓,覺得我把虛構和非虛構的東西混在一起了。但是我會覺得對於學生來講,這本書會是非常重要的教學材料。我記得我有看過一部美劇,裡面有個治療師當他和垂死的病人工作的時候講到貓,我們講貓有8條命,如果純粹從文學的角度或者從詩學的角度,我覺得這是我寫出來最好的文筆的東西,講的實際是一個真實的內容,講的是我和我媽媽之間關係的故事。我很好奇亞洲的讀者看這本書有什麼樣的反映,因為我知道亞洲的讀者被教育要非常尊重自己的父母,但是這本書裡面講我媽媽對我很嚴厲苛刻,我對她也是這樣的。這本書裡面還有一個故事,關於一位女士,她失去了她的丈夫,實際是關於哀傷很好的教學素材。當我重新讀我寫的書的時候,還有一個非常奇怪的體驗,當你到我這個年紀就會明白了,我的記憶力沒有像你們這樣好的,讀的時候我很好奇結局是什麼,因為我已經忘了結局是什麼。
【趙旭東】我們準備要按時結束,現在還剩四分鐘,時間真的是過得非常快。
【歐文•亞龍】真的過的很快。
【趙旭東】我們談得非常愉快。
【王浩威】我可否問一個比較個人的問題?現在在寫回憶錄,剛才亞龍也提到,他年輕的時候的死亡焦慮所以才去看羅洛•梅,我想說寫回憶錄本身和他面對年老本身是否有關係,包括死亡焦慮?他怎麼去透過寫回憶錄來面對他的死亡焦慮?這是他一直在講的我們都有的存在議題。
【歐文•亞龍】當然有很大的關係,但實際上我有這個方面的焦慮是從很久之前就開始的,當我寫《存在主義心理治療》那本書的時候,我就知道我在寫的就是死亡。我想對死亡瞭解得更多,所以我會和我的病人談論死亡,但是那個時候我們找不到一個辦法去談,他們也不談,我也不知道怎麼讓他們談。也許他們太害怕了,也許他們可以從中感覺到我自己對於死亡的恐懼。所以現在我掌握了不同的方法來和他們談,比如說我會和他們談他們的夢。
這就是為什麼我後來和癌症病人一起工作,因為對他們來說不得不談論死亡,死亡是他們必須面對的問題。那個時候當我開始帶癌症團體的時候,實際上在美國也是非常少見的。我當時有很多的團體,是乳腺癌的患者,這些女性知道她們無法達到治癒。當我和她們一起工作的時候,我特別焦慮,我開始有很多關於自己死亡的焦慮。
當我重新回顧我自己接受個人分析的700次裡面,我們一次都沒有談論過死亡這個話題。這對我來講是非常震驚的,因為我個人的死亡問題居然從來沒有在我的治療當中出現過。因此我意識到也許我要接受另外一種不同流派的心理治療,這就是我為什麼接受羅洛•梅的治療,也許他更願意公開談論死亡這個問題。於是在我們的治療中談論非常多,我也許讓羅洛•梅非常焦慮,但是我自己有學到如何更好面對看待我自己的死亡焦慮。
【趙旭東】談到死亡觀念,我5年前做過一個報告,中國特殊的傳統文化上面提出positive fatalism-積極宿命論,今天我非常有感觸。
【歐文•亞龍】我也想用這樣的方式來做結束,我覺得這種積極地看待死亡的方式,可以説明我們獲得更加豐滿的生活。有一次我在帶一個癌症病人團體的時候,有一位男性病人給我說,很遺憾,等到我生病之後,才知道怎樣生活。有很多的文學作品都有談到這情形。不知道狄更斯的作品你們是否熟悉?—(閃小春告訴亞龍,狄更斯在中國是非常受到歡迎的),他有一本書叫《歡樂頌》,其中講到過有一個吝嗇鬼叫斯古奇,他有三個死亡的天使,或者說三個死神來探望他。三個死神讓他去看未來的世界怎麼樣,看他的葬禮上沒有一個人來參加,也沒有一個人為他流淚,當斯古奇看到這部分以後,整個人完全改變了。我覺得我應該寫過這個故事的,可能在《存在主義心理治療》那本書裡面,一個吝嗇鬼轉化為很慷慨的人。
【趙旭東】我們要在這裡做結束了嗎?
【歐文•亞龍】我很享受這個對話,也很享受和大家一起聊天。
【趙旭東】快樂的時光總是轉瞬即逝。我現在來談一談我的印象,我們就可以結束。您今天的演講,我們的對談大概10萬左右的人觀看,影響非常大。
【歐文•亞龍】他們都是誰?
【趙旭東】很多的心理諮詢師,心理治療師,醫生,還有很多業餘愛好者。
【歐文•亞龍】真的是10萬,我從來沒有對這麼多人講,我以為就你們三個。
【趙旭東】所以要感謝現在的IT技術,傳播了你們的思想。
【歐文•亞龍】謝謝你們的幾位讓我今天的會談這麼輕鬆,這麼放鬆。
【趙旭東】我現在更加體會到,您是一個偉大的講故事的人,您今天講了很寬很深的學術,還講了您自己的故事,所以我能夠感受到您曾經強調過的幾點心理治療師的特質,就是真誠、透明、共情。談到兩點非常重要,我原來看過您的東西,強調兩種治療的力量,一種是powerful ideas,另一個是powerful intimate connections。所以我看到的就是您又重視個體的問題,又重視團體的問題,讓我們學到了很多。
另外我非常高興知道您是2009年佛洛德國際心理治療獎的獲得者。我和一位德國同事代表很多我們中國的同事領取了2008年的集體獎,因為我們把精神分析、認知行為治療CBT、還有系統家庭治療引進了中國,現在在臨床上得到了應用,所以非常高興。
我剛得到最新的數字,有19萬觀眾,對我們也是第一次的體驗,非常的高興,非常興奮。
【歐文•亞龍】我今天非常榮幸有這麼多人看和聽,有這麼大的影響力。
【趙旭東】我今天很有信心,下一次還能請您給我們講課,您的健康狀況非常的好。您的記憶非常好,反應很快。
【歐文•亞龍】我希望我今天沒有把所有的故事都講完,要不然下次就沒得講了。
【趙旭東】您是一個榜樣,成功老齡化的榜樣!(An example of successful aging)
【歐文•亞龍】我非常榮幸,謝謝你們,謝謝你這麼說。
【趙旭東】我忘了感謝翻譯,同濟大學人文學院的博士生閃小春,幹得非常棒,謝謝你!
【閃小春】非常榮幸!
【趙旭東】希望你很快學成回國!我們明天下午成立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心理學系,歡迎你回來!
活動開始日期:2016-06-15
活動結束日期:2016-12-31
|
| |
|